2025-09-11 15:27

何媛
编者按
20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将迎来建院一百周年。百年时光里,紫禁城从皇家私有之地,转变为公共文化空间——如今,参观者既能走进其中参观古建筑,也能欣赏院藏的各类珍品。
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承载着特殊意义。本报从今日起推出特刊“新章——故宫博物院百年”,每周一期,带公众一同探寻故宫博物院历史上的五个“第一次”。
1924年12月至1930年3月间进行的故宫物品点查,是中国文物史上规模空前的清点登记工作。这场历时六年的系统性工程,不仅完成了对历代皇家收藏的国有化确认,更开创了中国现代文物管理的新范式。

点查人员在乾清宫前合影
 养心殿点查时录入的“吕一号”祖丁鼎
养心殿点查时录入的“吕一号”祖丁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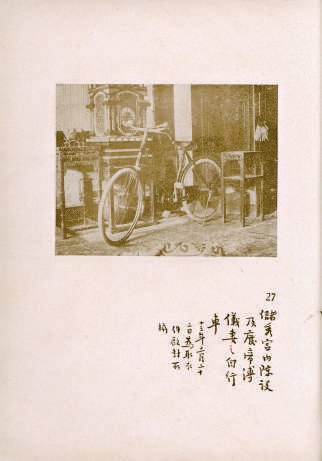 储秀宫内婉容自行车登记在册
储秀宫内婉容自行车登记在册
警察不到不予点查
1924年11月5日溥仪出宫后,社会上随即展开了关于清宫物品究竟属公产还是私产的争论。著名报人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国民的心声:“宫中各种古物,何者应归溥仪,何者应归国民,应纯以有无历史的价值,及与文化有无关系为标准。大抵小件珠宝、金银、皮货、绸缎之类,皆可划归溥仪。而大件重器,及与历史文化有关系之金石书画等,数千年国宝所流传,与爱新觉罗全无关系,断难据为私有,而应作为国家之公产,全数陈列,以供研究历史美术文化者之参考。”
1924年11月19日,北京8所高等学校的代表召开联席会议,赞成组织善后委员会清理清宫物品,并就古物的处理通过如下决议:“关于清室古物宝器,希望成立一完全美满之图书馆、博物馆,由国家直接管理,并邀集各机关参加监视,期在公开保存,俾垂永远。”因此清室善后委员会应运而生。
1924年11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筹备就绪,宣告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为李煜瀛,委员有:汪兆铭(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鹿钟麟、张璧、范源濂、俞同奎、陈垣、沈兼士、葛文濬、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自绍英以下5人属于清室)。监察员除京师警察厅、高等检察厅、北京教育会是法定监察员外,还特聘请3人,分别是庄蕴宽、吴敬恒、张继。
1924年12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通过《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件规则》,规定点查事项人员组成、点查分组安排、点查时间等;点查物品时,以不离物品原摆设之地为原则,如必不得已须挪动位置,点查结束后,还要归还原处,同时不得移至室外;登录时,每种物品上均须粘贴委员会特制的标签,贵重物品需要详细记录其特异之处,必要时,需要拍摄或用显微镜观察,防止抵换。会议决议于当月22日(星期一)下午在神武门城楼上召开点查预备会,23日正式开始点查清宫物品。
12月23日上午,担任点查清宫物品任务的人一早到神武门集合。从现存档案“点查组单”可以看到,当天点查组长是陈去病,负责查报物品名目的是徐鸿宝、马衡,负责物品登录的是陈宗汉等3人。当天理应到场的警察未到,因此这天没有点查。“点查组单”特地批注:“本日因警察未来,未实行点查。”正式点查工作至24日上午才从乾清宫、坤宁宫开始。
清点出文物超百万件
到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时,点查登记造册的文物已有一半,后来点查工作多次停顿。到1929年3月秘书处成立,未点查的剩下宫内皇极殿、颐和轩一部分,以及宫外大高玄殿、实录大库等处。于是秘书处商量各馆处人员,全体加入点查工作,每日分两组或者四组进行。
1929年5月,颐和轩东间点查完毕,1929年8月,皇极殿及盆库点查完毕。至此,宫内物品均点查完毕。1929年9月,仍继续点查宫外各处,11月,大高玄殿点查完毕,12月,接着点查实录大库、东西二库。至12月底,宫外未点查的地方,仅剩銮舆卫、帘子库两处。1930年3月,完成銮舆卫、帘子库的点查。至此点查告一段落。
每次点查,先由组长和监视员率同组员、军警验封启门入内,依次点查编号登录,碰到特别的物品,需要由事务员详细记录并且拍照,物品点查后仍归原位。当日点查结束,组长复查无误,在物品登记簿签字再离开。每次点查退出时,组长同监视员将内外各门照旧上锁,各门加贴组长签字的锁封、门封。点查结束之后,如果有箱柜等,也必须上锁加封,人员退出后,各钥匙交还事务室。
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点查后的文物信息被及时整理成册,陆续出版了《故宫物品点查报告》6编28册,每册都附有点查清宫物件规则、点查情形、封锁情形和点查人员统计表。点查人员统计表包括:点查日期、点查时间、点查组号码、组长姓名、监视姓名、军警执勤人员姓名、参加点查人数、点查物品起讫编号、点查件数、照相张数。据不完全统计,清宫遗留下来的文物共有117万件。
溥仪是居住在紫禁城的最后一位皇帝,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品时,溥仪及相关人员在紫禁城居住期间的物品也被详细登记,有眼镜、彩电灯、壁上电话机、嵌宝石西洋钟、洋伞、洋式圈椅、洋画挂镜、洋式枕、洋便帽、西餐刀叉、西洋画、留声机、显微镜、假胡须、钢琴、英文打字机、网球拍等。溥仪等居住在后廷区域,为消磨时间,会在宫内骑自行车、打网球、拍照等。溥仪、婉容等人喜欢给别人拍照,也喜欢自己拍,故宫的老照片中有多张溥仪、婉容等摆弄照相机的照片。
溥仪15岁时,听英文教师庄士敦讲起电话的作用,就叫内务府在养心殿也装上一个。有一次溥仪给庄士敦提到的胡适博士打电话,溥仪说“有空到宫里来”,后来胡适找庄士敦核实确实是“皇上”打的电话,为此专程来了一趟紫禁城。
婉容居住于储秀宫,但翊坤宫与此处相连,因此翊坤宫内点查的物品也能反映婉容的爱好习惯。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翊坤宫时,发现有西式梳妆台、咖啡饮器、留声机、钢琴、英文书、西洋带穗小挂镜、电话机、香水胰皂、小电影机、洋式元宝椅、手电灯、电灯、自行车、洋钟等,这些西式用具反映出,末代帝后的生活与之前清宫生活大不同。
点查物品时点查出多辆自行车。溥仪与婉容结婚时,溥仪的堂弟溥佳送给他们的新婚礼物是一辆自行车,溥仪练习了几天就会了。他后来又买了许多自行车,为了骑自行车方便,命人锯断宫内门槛二十余个。至今,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溥仪、婉容使用过的一辆英国三枪牌自行车。
留下了“国宝公有”精神传统
1925年10月10日,紫禁城转变为故宫博物院,这座巨大的建筑不再是皇室私有,而是变为公共的、大众的场所,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博物院开放当天,北京万人空巷。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中写到开院的情形:“我看到一位先生,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份报纸,走到门口,伸着头向里探望。他也未必决定是不是进来看看,可是,被后面人一挤,就挤进来了,他成了‘夹心饼干’的馅子,夹在那里,缓缓移动,有时他伸伸脖子,向展览柜中望望,我想他也未必看到什么,然后被夹了出去。”
文物藏品是博物馆的基础,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清宫物品的点查及后来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秘书处等机构继续进行点查工作,为故宫博物院建院后的各项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物品点查过程中确立的“编号规则”“登记物品”“留存影像”等流程,为后来我国的博物馆藏品管理打下了基础。
点查工作最重要的影响是确立了文物共有的理念,通过邀请社会各界参与监督,公开出版《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打破了历代皇室“秘不示人”的旧传统,开创了文物属于人民的新传统,这种理念的确立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场点查,不仅留下了百万件文物的原始档案,更留下了“国宝公有”的精神传统。在数字化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回望当年学者们用最原始的方式逐件清点的身影,更能体会文化守护的艰辛与执着。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延伸
养心殿里数珍宝
郑诗琪
养心殿位于故宫内廷西六宫南侧,始建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初名“未央宫”,后更名“养心殿”。清雍正皇帝即位后移居此殿,经乾隆朝进一步改建与扩建,养心殿逐渐取代乾清宫,成为清代皇帝日常批阅奏章、召见大臣、处理政务的核心场所。此后,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诸帝相继以养心殿为寝宫和理政之地,历时近两百年。可以说,养心殿的物品都是清帝最喜爱的。
养心殿物品点查工作于1925年6月26日正式开始,历时七个月,至1926年1月28日止,共计点查108次,物品4036套六千余件。
1925年6月26日早晨,养心殿物品点查工作正式拉开帷幕。易培基任点查小组组长,俞同奎任监视,参与的军警为宋德全与白桂亮,还有监视员、助理员、顾问、事务员书记等7人,全组共计11人。
关于养心殿的物品点查,编入《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三编第四册。《故宫物品点查报告》遵循严谨的记录规范,各宫殿按所处路线归于“编”,再按宫殿在该路线的方位归于“册”。养心殿面积较大,物品号数过多,便又以点查物品所在地为标准,分五卷列之。
点查的宫殿依《千字文》编列字号,如乾清宫为“天”字、坤宁宫为“地”字,养心殿则列为“吕”字。“吕”字后面的中文号码代表点查物品的号数,阿拉伯数字则代表每一件物品包含的分号号数。如“嘉靖款青花十六子图盖罐”,点查编号是“吕一〇二七”,“吕”代表养心殿,“一〇二七”表示该文物是第1027号点查文物,没有阿拉伯数字的分号则表示文物仅有一件。“青玉蟠夔纹黼佩”是“吕一七四-1/2”,表示黼佩是养心殿第174号点查文物,但此佩形制为两件一套,另一件为“吕一七四-2/2”。
养心殿珍藏了哪些文物?是否有稀世之宝?翻开点查账册,赫然可见“吕”一至十号所列之物:祖丁鼎、散氏盘、碧玉雕龙香亭、碧玉兽炉、洋磁花插、楠木桌、成套文房用品、嵌乾隆御题红木字红木屏风、宫扇、红木茶几,品类琳琅,横跨古今,既有商周重器,亦有当朝精工,堪称宫廷收藏缩影。
“吕一号”为一件名为“祖丁鼎”的青铜鼎,其名称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典藏资料系统”中的“婴祖丁鼎”极为相似。然而,由于账册中仅记录了器物名称,未附图片、尺寸、铭文拓片或其他可供比对的详细信息,二者是否为同一器物,一时之间,难以断定。
但是通过检索相关资料,真相水落石出。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精彩一百 国宝总动员》中明确记载:“婴祖丁鼎的器型宏硕、气势雄浑、纹饰精美、铭文劲健,是(台北)故宫现藏最大最重的铜器。著录号为吕1,可知原藏在清宫的养心殿。”这段关键信息不仅确认了该鼎的重要地位,更直接将其与点查账册中的“吕一号”青铜器对应起来。由此可以肯定,点查报告中所载的“祖丁鼎”,即为今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婴祖丁鼎”。二者名称虽略有出入,应为不同时期命名习惯导致。这一发现不仅厘清了文物传承脉络,也凸显了历史档案与实物著录相互印证的重要性。
相较于“吕一号”祖丁鼎在公众视野中的相对“小众”,“吕二号”西周晚期的“散氏盘”则广为学界与公众所知。散氏盘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因其确切出土地点不详,散氏盘亦被称为“夨(zè)人盘”,盘内底铸357字铭文,内容叙述夨国侵犯散国无功,以致割地抵过,详细记录了转让的土地范围及参与履勘的官员职名,具有极高的历史与学术价值。
观察前三卷的点查物品名称可知,它们是依据在养心殿不同殿宇内陈设的位置来分类登记。可是《溥仪取物账》与《养心殿铁柜》这末两卷,从名称上看,显然不再遵循这一空间逻辑,其编纂方式为何独辟蹊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特殊历史情境?
翻阅《溥仪取物账》可以看到,点查人员在此清晰记载了溥仪被驱逐出宫后,他曾于1924年12月两次派亲信返回养心殿提取物品。根据登录账册显示,两次提取物品数量逾190件(套),所取之物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印章、御批通鉴、洋书、洋墨水笔、千里镜等文房器具;另一类为刮胡刀、面盆、背心、马褂、皮袍、斗篷等生活用品。
而《养心殿铁柜》一卷的由来,则源于点查中的一段特殊插曲。当清点到养心殿正殿时,一只铁柜怎么都打不开,这一情况让现场人员犯了难。考虑到整体进度,点查人员决定将其搁置,以待来日查验。
1926年1月28日,养心殿整体点查工作告竣后,点查人员重启特殊物品点查,先前“顽固”的铁柜顺利开启,内部物品重见天日。经仔细点查发现,柜内物品总数达七百件左右,含有朝珠、带扣、手镯、耳环等珍宝饰物,应属溥仪之私物。此次补查工作于次月24日结束,相关物品亦被逐一登记入册,单独成卷,遂有《养心殿铁柜》之目。
1925年7月31日,点查人员发现一匣盛有1924年春夏间溥仪与金梁、康有为等密谋复辟的来往信件,即“卷一 养心殿”中“吕五三三 金梁奏折等”,内里共8封信件——《内务府大臣金梁条陈二事折》《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金梁条陈三事折》《金梁条陈四事折》《金梁列举贤才折》《康有为请庄士敦代奏游说经过函》《金梁为江亢虎请觐折》《江亢虎致金梁请觐溥仪函》《江亢虎致金梁再请觐期函》。
同日,点查人员还在养心殿发现一份“赏溥杰字画单”。溥仪小朝廷时期,以赏赐、出借名目盗运出大量宋、元、明版书籍以及唐、宋、元、明、清书画。东晋顾恺之《列女图》、隋代展子虔《游春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北宋李公麟《五马图》、北宋崔白《寒雀图》、北宋赵佶《瑞鹤图》、元代王蒙《听松图》、明代祝允明书《前后赤壁赋》等翰墨丹青巨作皆然在列。
清室善后委员会通过系统点查养心殿物品,明确记录了文物的存藏地点和保存数量,为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及其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