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17 0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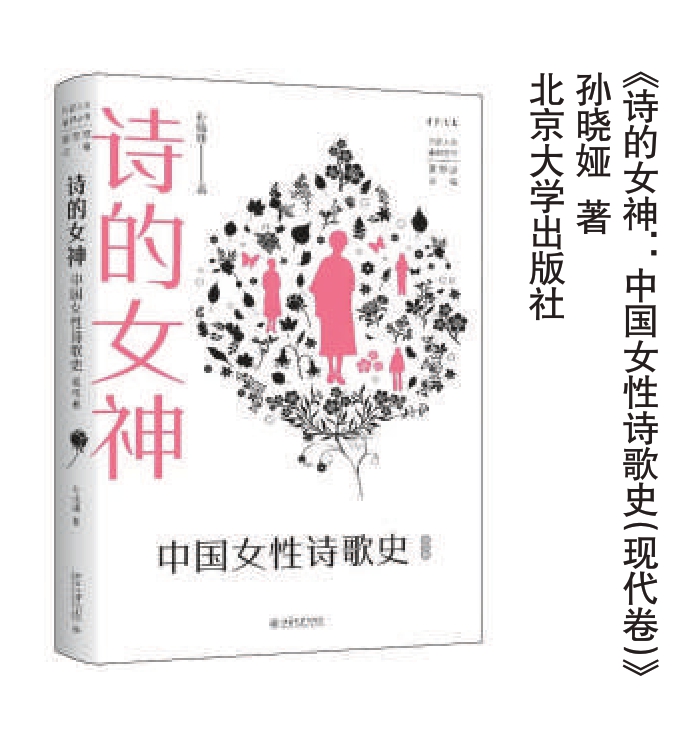
中国诗歌的传统源远流长,“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其艺术体式和审美内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诗歌作为民族心灵和个体情志的艺术表现形式,承载着绵延久远的中华文明,记录了历史文化的变迁,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力量,是中国文学史中最具生命力和代表性的文学形态。在中国诗歌史上,无论是以“抒情言志”为传统的中国古代诗歌,还是现代主义诗潮导向的新诗,男性文人士大夫或现代知识分子都是主要的诗歌创作主体,而作为镜像共生的女诗人和女性诗歌一度被湮没在诗歌历史长河之中。
一直以来,女性诗歌的概念边界都比较模糊。广义地讲,女性诗歌即女诗人的诗;狭义而言,女诗人写作中表现的“性别经验”和诗歌的“性别”特质,才是“女性诗歌”的基本条件。数千年来,中国女性诗歌经历了上古时代的高地、中古时代的低谷,经过近古的明清直至现代与当代,走过跌宕曲折的创作历程,直至当下,女性诗歌创作日渐繁盛,呈现出纷呈迥异的发展状态。
新的文学体制和新的文学精神,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与文化改革登上历史的舞台,“女性”一词也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女性文学”和“女性”两个概念最初都出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此之前,指称女人的词语,都是对应着具体的处在家庭人伦关系中的女人。“女性”一词的生成,标志着女性以独立的人的身份在社会上出现。在古代女性诗歌发展史上,女性诗歌固然有独立的发展规律与轨迹,但多是作为文人士大夫文学的附属品而存在,多被定格为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镜像反映。
与古代女性诗歌及晚清民初女性文学创作不同的是,五四时期,不仅女作家群的崛起富有历史意义,而且从文学内部机制看,中国女性文学由萌生、发展到形成独立的品格,自产生之日起就孕育着现代品质。她们不甘屈服于男权统治,呼唤“女人的权力”,陈衡哲、冰心、陈学昭、石评梅、陆晶清、苏雪林、白薇等一大批女诗人浮出历史的地表。相较此前,五四女诗人不仅体现出迥异于古代女诗人的新视野和新精神,而且从语言范式上和艺术审美品格等方面也完成了转型,只不过这一过程充满了挑战和矛盾。
作为第一批留学海外的女大学生作家的代表,新文学最早的女性拓荒者陈衡哲说过,她们那代人,本想着将命运掌握在手中,却又害怕背离传统。这种矛盾是五四时期大多数女诗人自身经历与精神体验的写照——她们一方面浸染于五四新的时代思潮,即“人的觉醒”,个性独立解放,另一方面在女性深层意识里又受到传统意识、家庭和亲情等对她们精神与命运的箍制羁绊。体现在诗歌创作中,一方面追求光明和自由,表达个性解放等强烈的时代叛逆精神;另一方面又从家庭、亲情、自然中寻觅爱的辉光,在扭结的矛盾中完成了从形式革命到思想革命的转变。
冰心是第一批国内大学生中最具代表性的女诗人,她在小说、诗歌和散文方面均取得斐然成绩,相应地,她分别介入或开创了“问题小说”“繁星体”“冰心体”。其中“繁星体”的小诗成为连通另外两类文体的桥梁,她的小说富有哲理和诗性,散文则是小诗的放大。在冰心的全部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繁星》《春水》中的小诗。这两部诗集分别为中国新诗史上的第六、第七部个人诗集,它们是中国新诗的两块奠基石,也奠定了冰心在中国诗坛的地位。
历经第一个十年的洗礼,较新诗草创期女诗人凤毛麟角的实况,到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女性诗歌创作呈现出繁荣景象。一方面,它延续着五四启蒙话语,另一方面,多元文化生态的促进与女诗人日益自觉强大的创作心理,使30年代女性诗歌臻至前所未有的高峰。从事新诗创作的女诗人数量陡增。可以断言,这十年确实是女性诗歌创作繁荣期。
不过,20世纪30年代女性诗歌创作的高涨与此后的迅速冷却、被遗忘形成鲜明对比。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女诗人本然钟情于“个人化”和“私人化”的诉说方式,与彼时的时代主潮发生冲突,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终将被边缘化的历史命运。当抗战的硝烟弥散中华大地,出版业昂扬的发展势头骤然跌落,国人的阅读心情改变时,女诗人的创作便失去了生存和阅读的空间。如此,承续五四启蒙而歌唱的花自然无可挽回地凋散了。与革命话语相并行的,是20世纪30年代女性诗歌的另一审美维度,即在私语倾诉(或对话)中自觉彰显女性意识。代表诗人有林徽因、陈敬容、王梅痕等。
林徽因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从后期新月派诗风到现代性写作两个探索阶段,自1931年4月第一首新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刊发于《诗刊》第2期,就体现出诗体自觉意识,她一出手即至成熟。如果说冰心的早期诗歌创作有意于面向广大读者,那么林徽因则驻于自我抒怀。林徽因早期诗歌多涉及爱情,捕捉自然和心理片影,长于刻绘现代女性的诸美,自觉躬行新月派的三美艺术主张。其广为流传的《笑》《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等诗作中,句式流萤般轻巧,语言唯美清透,结构复沓回环,叠字押韵,翩然明媚。林徽因的诗歌蕴含着典雅优美的古典气息与谪仙低首的空灵美,将女性在日常生活和情感经验中的碎片浸润禅意美,柔婉中蕴蓄着宁静与和谐。就此而言,林徽因有别于前期或同期可以彰显女性意识和身份的女诗人,她在诗歌创作中忘却自己的女性性别,消融于男性世界之中,这恰恰源于她的性别平等的观念和强大的自信。可是,私人的世界再迷人也会被耗尽,她的中后期创作逐渐从个人情感抒发转向社会人生与日常现实书写,并自觉于新诗现代性探索。
陈敬容是中国新诗史中十分重要而又略被低估的女诗人,她与生秉具桀骜的诗人气质,心性敏感倔强,孤独之感与迷茫之思构成其早期诗作的主流情绪,其30年代诗歌创作主要有两个情感取向:其一是背井离乡之后流落异地的思乡之情,孤独忧郁;其二是理想的无期,对茫茫人生的迷惘,渴望被理解慰藉的少女心态。这一时期的诗作在私人独语空间拟构出潜在的对话者,对话者的非人化、色彩的情感化以及大量无解疑问句式的应用,都体现出诗人的别具匠心。
陈敬容和郑敏是20世纪40年代女性诗歌创作的标志性诗人,“两叶”(九叶诗人)并进,为诗坛呈奉多首现代诗风浓郁的经典诗作。她们有诸多共性,如才智不凡,具备广博的中西知识背景和现代诗学谱系,不向公众和时代献媚取宠,警醒于现代价值理念和现代审美特征,她们的诗作兼采学院气息、精英化特征和现实关怀。她们跨越了“学院”的藩篱,具有强烈的时代关怀与历史反思精神。
(作者为博士生导师,长城学者,首都师范大学青年燕京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