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3-09 2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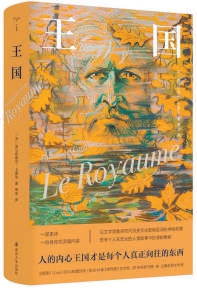
“我一直以写作为生,最开始的时候做记者,后来转行写书,给电视剧做编剧,自力更生让我有些自豪。”法国作家埃马纽埃尔·卡雷尔在小说《王国》里这样写,如同自叙。只不过小说里的卡雷尔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作家,并把婚姻不幸归结于此。现实中的卡雷尔曾获费米娜文学奖、法兰西学院文学大奖。他的《王国》提供了一种自我书写与神话重述相互叠合、神游历史与前贤对话的全新语境。
卡雷尔试图把原本属于信仰的故事解放出来,用世俗生活的道德信念进行重塑讲述。在他看来,道理和伦理比教条适用更广,常识与原则对于人类生活更为根本。小说《王国》实质上是对不同民族的文化阐释与历史评注,它试图找到异质文明相互对话的可能。故事中原本固定的使徒语境,被文学叙事赋予全新意义。作家重估了犹太人、罗马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在历史中的遭遇与对抗,并从文化心理上洞察民族冲突的根源。

小说叙事者是作家、历史学者与调查员的三位一体:他一边重读神圣文本,一边回溯使徒之路。卡雷尔用纪实文学的外壳包裹小说主体,叙事者与作家名字一致,身份叠合。“我”每天都会写下对某些段落的思考,“零零散散的笔记一共写了二十多本”。他用怀疑论对人物进行肖像式批评,又以不可知论对经典进行探寻,破除了诸多迷信。可以说,从中世纪知识分子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都在争夺对经典的解释权。卡雷尔的小说,也是以小说争取阐释的一种手段。它形成《王国》的两种内在风貌:一是作为历史研究的笔记,二是作为地理探访的游记。
“我”思索读到的内容,每天写几行字总结自己的思考。如书中对人物气质的譬喻:约翰这匹纯血马,上来就给下马威,马可则像健壮的佩尔什马。又如以柏拉图灵肉观念、洞穴隐喻去理解生活不如人意,真正的生活在别处。“因为人难免犯错,肉体终将腐败。”
另一方面,游记则是揭示人物精神的方法。卡雷尔以荷马的语境反向阐释了保罗的理想。奥德修斯的行纪是向人世回归,返回人的境况。保罗之行说明挣脱凡人生活才是智慧。然而,“世间有群幸福的人,他们热爱生活,生活给予回馈,他们除了眼前的生活什么都不想要”。“永恒不可期,它不是人类共同命运的一部分。人生不完美、转瞬即逝、让人失望,可它是我们唯一要珍惜的东西,它是我们必然总会回归的方向。奥德修斯的整个故事,甘做凡人只为拥有完整人生的人类的整个历史,讲述的都是这样的回归。”
作家并不想探讨超越思考和经验范畴的东西。“在母亲的眼里,灵魂的事跟性一样,都不能拿来讨论”,叙事者只是把超验的故事视为一种奇幻文学。这涉及到书写的心态:一个热衷于希腊神话的人,并不见得真正相信希腊诸神的存在。相反,书中看重的乃是伦理的通约——人要向善,不要从恶,这并不是什么新道理,而是古希腊人和犹太人都懂的准则。这条准则本身囊括了律法内容,“你不希望别人对你做的事,你就不要对别人做”,要做普通人,安贫乐道,它甚至与儒家价值也高度契合。
在书中,历史和神话,文本和遗迹之间充满反差断裂。在我看来,小说是对历史幻象的弥合。如果对照现实,就会发现生存的寓言。作者写道,整部以色列的历史像是由一连串警告构成。他们受到威胁、警告、判决,却总在最后一刻撤销,而被赦免罪责。以色列像走了历史的“后门”,每每都能危机公关,幸免于难,这背后有股力量叫作:应许还乡。历史上即使巴比伦人攻陷了耶路撒冷,也允许流亡的犹太人归乡。
卡雷尔在文本里找寻日常行为的准则,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启发。“我们就是要好好咀嚼这些段落。它们在训练注意力,训练耐心,训练我们谦逊的态度,特别是谦逊这一点。”从中,我们发现了细读文本与重述故事的内在关联,二者同归于作品的核心——即人物的信念。文本里的话不是随便说说,“这绝对不是单纯地讲故事:这是灵魂之战中的宝贵指南。”与使徒的虔诚相通,作家要坚信文本里存在真理与意义。
“对这些段落,特别是这些难啃的东西,我下定决心,誓不退缩。”它唤起作家的良知和批判精神。在我看来,《王国》的意义就建立在舍斯托夫的命题之上,即耶路撒冷和雅典这两极世界的调和。前者象征一种启示价值,后者则代表一个理性世界。作家意欲建立一个能够搁置判断、进行批判重思的辩证精神王国。人物从“我相信”转变为“我认为”,从精神危机、内心费解再到精神震动,意味着重新理解、发现人类“真实重要之事”。
(作者为书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