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末,与家人在泰国清迈旅行,住在一间由本地人经营的民宿里。漂亮的小院种有密密的绿竹,露天的茶水吧旁摆着长条木桌椅,供房客们休憩与社交。一日清晨,我照例起床后先在院子里泡茶——人一旦养成了习惯,就走到哪里都改不了,仿佛只有饮下一口热茶,一日才算开启。热情好客的泰国房东见我在喝茶,忙从橱柜里又拿出好几大包茶叶,说都是中国朋友送的,但他既叫不出名字,也不知其品类。
“哦,这是乌龙,这个呢是白茶……”我一一告诉他这些茶叶的特点与冲泡方法。“中国人真厉害!”他笑道,“因为你们中国是茶叶的发源地,所以我遇到的每个中国人,好像都非常了解茶!”
听他如此夸奖,有些惭愧起来。可以说“非常了解”吗?虽然我在岭南长大,当地茶俗风靡,得以日日与这“南方之嘉木”接触,除了喝茶,无事亦喜欢翻阅茶书茶典;平日做编辑,在咱们五色土也开设了一个“茗茶故事”专栏,甚至因此结识了一众茶友;但与玉瑶一同完成这本《杯中的故园:茶与中国人的风味生活》后,就越发地感觉到中国名茶包含折射的世界奇妙广阔。
历史长河顺流至今,茶早已渗透进了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方方面面,它也作为令中国人骄傲的“东方树叶”漂洋渡海、席卷全球,名列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这中间所蕴的山川之姿、历史之韵、文艺之美,不仅一本小书的容量只能撮其一毫,而每一杯茶汤的滋味——也都如玉瑶在“茉莉花茶”一章结语中所写的那样,“远未品尽”。

饮茶,除了把它当成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饮料外,我们还可以品些什么呢?
平日里,喜欢观察身边的饮茶者,在纵向的时间坐标上,感觉每个人的饮茶“阶段”或许各不相同:有的是年轻人,只热衷在办公室煮养生花茶,再放上红枣、枸杞等物,颇有点唐朝人煮茶放一堆佐料的“古韵”;有的是嗜茶者,每天都必须要喝一喝茶,用什么器具倒无所谓,喝到毛孔微张、两腋生风就心满意足了;还有的老茶客,用精致的工夫茶具,从早到晚行云流水般地泡茶,尝清淡口味的茶已无法感到满足,而要专饮些“浓苦如药”的乌龙与黑茶。因此,在“岩茶”与“白茶”的章节中,我曾发出过感叹:品茶,就像是在品人生。当美丽的花茶、清淡的绿茶、香甜的红茶一一如风景般从舌尖滑过,也许人到中年后,才会突然品咂出了乌龙与黑茶劲烈后的清芬。翻开故纸堆,看看,历史上也有一生惯饮“水清茶绿”的杭州人袁枚最终折服于武夷岩茶之下,亦有在广东任职的县令萧麟趾就是喜爱盖碗蒸青,坚持入乡但不随俗。滋味万千的茶汤中,贮藏着人生趣味,恰就在这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故事。
若再从横向的地理坐标来看,每位饮茶者的偏爱与习惯,也俨然构成了一幅幅中国的茶叶江湖风情图,而“故园”就似是那画心之一。欧阳修与黄庭坚热衷为江西老家的双井茶代言;绍兴人陆游四处宦游时总随身带着的故园茶日铸;陆游的老乡张岱不仅品尝日铸,还上手改造,创出新品;清代名臣陶澍吟咏家乡安化千两茶的“霸蛮”之气,渴望以耿介之臣的身份扭转乾坤;东坡则是以武夷岩茶自况,在其中安放着自己的精神理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与物,草木与人生的故事交汇,又诞生了更多的文化诗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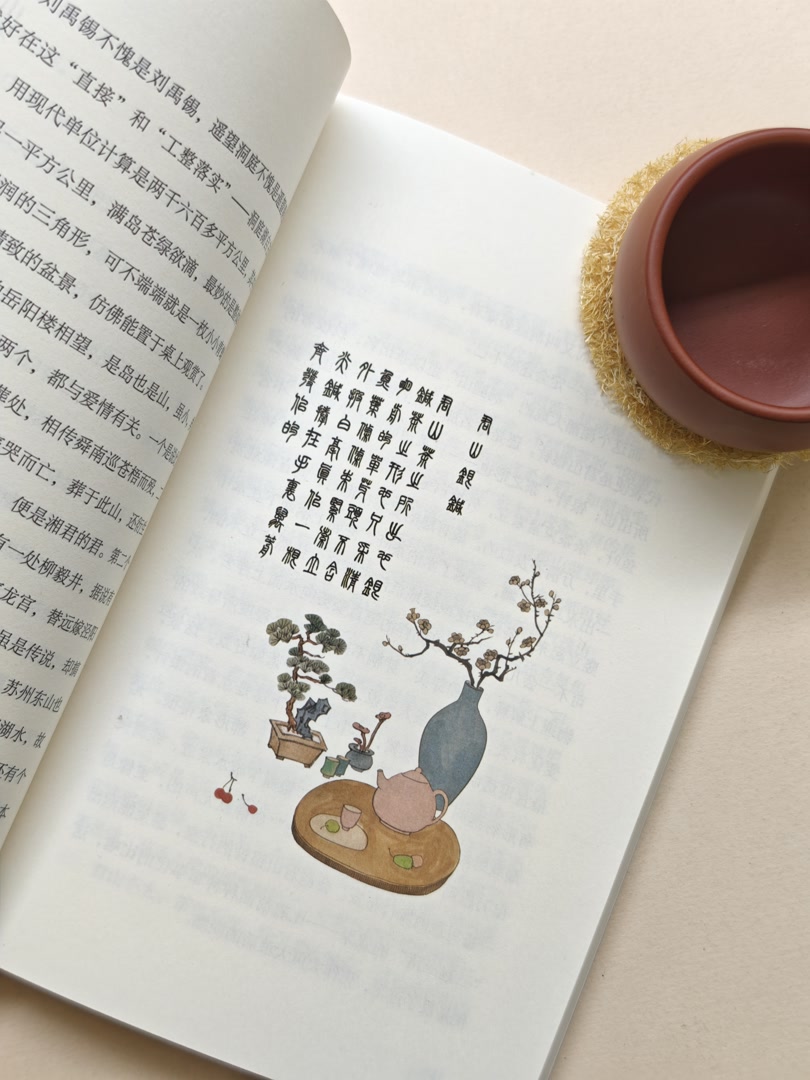
“茶叶江湖风情图”品起来也是极有趣的,它时刻都有可能在身边展开,即使是在五色土编辑部,也常能看到缩小版的图景:来自神奇闽地的杏珏称武夷岩茶为“乡愁之水”,有北京的前辈却独爱“用大搪瓷缸子喝茉莉花茶”,每个中国人与茶的交往,都是一部那么独特的饮茶小史。
我与玉瑶就这么边读边看边品,遥遥追慕着陆羽、陆游、苏轼、张岱等爱茶人的身影,述说着中国的名茶故事,听古人今人汲水煮茶的声音,许多属于我自己的回忆居然也纷至沓来,才发现,原来茶早已融入了我的生命,人生每一页都有点点茶香相随。尤其是离开祖国远游的那些时日,能随身携带的茶叶,就是一方方最小单位的故园——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无论何时何地,中国人只要捧一杯热茶在手,何处不是家?
这也是我们在挖掘名茶背后的文化与内涵时绕不开的,茶与饮茶者之间的情感。陆羽之后,茶因与文化联结而增添了美,又因为一代又一代人对其投入的深沉感情,茶的世界变得更加动人了。
但归根结底,我是因为喜欢茶才喝茶并写下这些文字的。有不喜欢喝茶的中国人吗?肯定是有的。但想奓着胆子化用一句稍嫌武断的话:“世界上只存在喜欢饮茶的,和不知道自己喜欢饮茶的中国人”。原话中代替“饮茶”的是“民乐”,当然也可以是“京剧”或者“书法”——意思就是这些传统文化的“血脉觉醒”,对许多人来说,有时只是时候未到而已。
赵朴初茶诗说得好:“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不如,就从现在开始喝茶吧!










